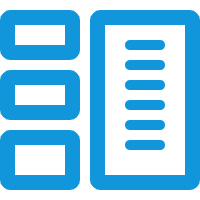讨论 尽管多模式治疗改善了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CTEPH)的预后,但对药物治疗患者的危险分层仍不尽如人意。当前的模型主要基于肺动脉高压(PAH),其预测能力有限(在我们的队列中,Harrell's C-index 为 0.59–0.71),这与 Stubbs 等人报告的有限性能(C-index=0.62)一致 [18],并且严重忽视了系统性炎症。本研究通过识别和验证独立的预后炎症生物标志物 sST2 和 IL-6,填补了这一空白,并证明将其添加到现有的风险模型中可以显著提高药物治疗 CTEPH 患者的预后区分度(例如,将 COMPERA 2.0 的 C-index 提高到 > 0.8)。这使该组合成为个性化管理的实用工具。被识别为高风险的患者,特别是那些两种生物标志物同时升高的患者,可以优先考虑强化治疗,包括重新评估介入手术、积极升级靶向药物治疗或抗炎治疗。相反,低风险患者的良好预后可能支持采用较不密集的策略,减少治疗负担和成本。这种方法可能弥合 CTEPH 扩展治疗选择与精准医疗之间的差距。
sST2 是 IL-1 受体家族的成员,作为 IL-33 的诱饵受体发挥作用。IL-33/ST2 信号轴在免疫、炎症和组织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失调在哮喘、类风湿关节炎和心力衰竭中已有充分记录 [32-34]。从生物学角度来看,sST2 与膜结合受体 ST2L 竞争 IL-33 结合,从而抑制后者的抗纤维化和心脏保护信号,促进促炎和促纤维化途径 [35]。近年来,sST2 已成为心肌应激和纤维化的强大生物标志物,提供了超越利钠肽的独立预后价值 [36-38]。在本研究中,我们证明 sST2 独立预测 CTEPH 的全因死亡率,突显了其在以广泛炎症和右心室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中的相关性。
同时,IL-6 通过 STAT3 介导的途径驱动内皮功能障碍和血栓重塑 [39, 40]。我们的发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炎症生物标志物的独特而互补的作用:sST2 作为心肺应激的指标,而 IL-6 主要介导血管炎症和血栓重塑。这种双途径模型解释了显著的生存梯度,其中两种标志物同时升高表明两种过程的放大和最差的预后。有趣的是,IL-6 升高而 sST2 低的患者预后比相反的情况更差,这表明在某些患者中,IL-6 驱动的炎症可能是主要驱动因素。
我们的研究设计还通过纳入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后的残余肺高压(PH)患者,推进了先前的研究——这一亚组在过去由于 BPA 证据不足和西方队列中 BPA 技术的相对有限应用而被排除在外。然而,在东亚,BPA 是治疗 CTEPH 的主流技术,并已在最新指南中推荐 [1]。将 BPA 后残余 PH 的 CTEPH 患者纳入本研究,与当代指南和登记数据一致,显示 BPA 和 PEA 后残余 PH 的发生率相当 [6]。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纳入了 BPA 后出现残余 PH 的 CTEPH 患者,这与 Stubbs 等人的方法一致 [18]。
尽管有这些优势,但仍需考虑几个局限性。首先,使用全因死亡率为终点,虽然客观且避免了判定偏差,但可能包括与 CTEPH 无关的非心血管事件,从而稀释生物标志物与结局的关联。然而,我们的 Cox 模型调整了关键的非心血管合并症(如活动性癌症、中风、肾功能不全),这加强了观察到的关联主要由 CTEPH 相关死亡率驱动的推论。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通过裁定特定原因死亡率来确认其与 CTEPH 心血管死亡的具体关联。其次,尽管这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并包括了一个来自不同地理和人口区域的独立外部验证队列,但在更广泛的多民族队列中进一步验证将有助于完全建立我们提出的生物标志物组合的普遍适用性。第三,这项研究是对炎症标志物在药物治疗 CTEPH 患者中预后作用的初步调查。作为初步探索,炎症标志物仅在基线时测量,随访期间未进行纵向再评估。这一局限性排除了对生物标志物动态变化及其与疾病进展和结局演变关系的分析。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并加深理解,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纳入连续生物标志物测量,以验证和细化这些发现。最后,此处得出的临界值具有平台特异性,在临床应用前需要进行本地校准。尽管如此,sST2 和 IL-6 作为连续变量的稳健预后表现(表 S2)提供了明确的生物学依据和实用的路线图,为本地验证工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sST2 和 IL-6 是药物治疗 CTEPH 患者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结合 sST2 和 IL-6 的组合在药物治疗 CTEPH 患者的风险分层中表现出优越的性能,并在整合到现有风险模型中时提供了增量预后价值。这些发现强调了系统性炎症在 CTEPH 病理生理中的关键作用,并突显了炎症生物标志物在该人群中细化风险评估的潜力。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开发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治疗算法,并评估针对 IL-6 和 sST2 的治疗疗效,最终推动 CTEPH 精准医疗领域的发展。
方法 研究人群 这项回顾性、多中心、双队列研究于 200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在连续药物治疗的 CTEPH 患者中进行。发现队列包括来自上海肺科医院(2009-2013 年)和阜外医院(2013-2021 年)的患者,验证队列则包括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2011-2021 年)的患者。发现队列和验证队列之间不存在患者招募、临床人员或实验室流程的重叠。
患者符合以下标准即可入组:(1)年龄 ≥ 18 岁;(2)根据 2015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欧洲呼吸学会(ESC/ERS)肺高压诊断和治疗指南 [25] 的标准确诊为 CTEPH,包括通气-灌注不匹配、肺动脉造影结果和右心导管检查(RHC)的血流动力学确认(静息时平均肺动脉压 ≥ 25 mmHg);(3)分类为“药物治疗 CTEPH”,包括:(a)新诊断且不适合介入手术的初治患者,或(b)PEA 或 BPA 后仍有残余 PH 的患者,入组时 RHC 确认残余 PH(平均肺动脉压 ≥ 25 mmHg),与当代研究 [18] 一致。可操作性由包括 PEA 外科医生、介入心脏病学家、肺高压专家和放射科医生在内的多学科团队确定,考虑解剖病变分布、合并症和患者偏好。患者因以下任一原因被排除:(1)缺乏存档血浆样本用于生物标志物分析;(2)术后(PEA 或 BPA)平均肺动脉压 < 25 mmHg,这些患者不符合 2015 年 ESC/ERS 指南 [25] 和当代队列研究 [13, 18] 中关于残余 PH 的血流动力学标准。
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同意收集和使用他们的血浆样本进行研究。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研究方案获得了所有参与中心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上海肺科医院(批准号 K08-015C)、阜外医院(批准号 IRB2012-BG006)和广东省人民医院(批准号 GDREC2011094H)。
基线数据和样本收集 我们收集了详细的基线数据,详见表 1。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危险因素、合并症、临床参数、血流动力学概况和治疗情况。所有血流动力学测量均在诊断 RHC 期间获得。基线血浆样本在诊断 RHC 期间收集。所有样本在采集后 2 小时内处理,以 3000g 离心 15 分钟,分装后存储在 -80°C 直至生物标志物定量。
sST2 和炎症细胞因子测量 血浆 sST2 水平使用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的临床验证测定法(上海艾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国)进行定量,该测定法基于 Critical Care Diagnostics, Inc. 的技术。细胞因子水平使用市售的基于珠子的多重 Luminex 测定法进行测量。所有测定法均显示出可接受的精确度和准确性,并在部分样本(n=30)中与临床平台(Roche cobas 8000 用于 IL-6;I200 用于 sST2)进行了交叉验证,显示高度相关性(Pearson's r = 0.93-0.97)。所有程序均按照制造商的协议进行 [26]。详细信息见补充材料方法。
随访 随访通过定期门诊就诊、电话访谈或互联网咨询进行。生存时间从 CTEPH 诊断日期计算到死亡日期、最后一次确认联系日期或研究截止日期(2024 年 7 月),以先发生者为准。研究终点为全因死亡率,通过医院记录、死亡证明或与家属直接沟通严格核实。
引言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CTEPH)被归类为第四组肺高压(PH),是一种进行性疾病,特征为未解决的血栓栓塞闭塞、慢性血管重塑和升高的肺动脉压力,最终导致右心室衰竭和过早死亡 [1]。虽然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为 CTEPH 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治愈性治疗,但由于远端病变、合并症或其他考虑因素,高达 36% 的患者被认为不可手术 [2-4]。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已成为不可手术患者的替代治疗选择,但由于对其长期风险-效益特征和技术复杂性的担忧,限制了其广泛应用。此外,高达 51% 的患者在 PEA 或 BPA 后仍有残余 PH [5, 6]。对于药物治疗的 CTEPH 患者,包括不可手术患者或 PEA 或 BPA 后有残余 PH 的患者,预后仍然较差,3 年生存率为 70% [3, 6]。近年来,经过多次随机对照试验验证,用于肺动脉高压(PAH)的药物已被证明能有效降低肺血管阻力或提高 6 分钟步行距离,从而拓宽了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 [7-13]。然而,这些人群的最佳药物管理尚缺乏共识。随着 CTEPH 治疗选择的扩展,迫切需要制定一种精细化、目标导向的治疗策略 [14]。这一策略依赖于准确的风险分层,以指导治疗的强化、升级或降级。
最初为 PAH 开发的风险评估工具,如 COMPERA 和 REVEAL 2.0 模型,已在药物治疗的 CTEPH 中进行了评估 [15-18]。然而,这些模型存在性能不佳、依赖侵入性测量以及狭窄的生物标志物谱等问题,忽略了系统性炎症的关键作用——这是 CTEPH 血栓组织、内皮功能障碍和血管重塑的主要驱动因素 [19]。观察研究表明,包括白细胞介素(IL)-6、IL-8、可溶性肿瘤生成抑制因子 2(sST2)和半乳凝素-3 在内的炎症介质水平升高与 CTEPH 的严重程度相关 [20-24]。尽管有这些机制见解,但循环炎症标志物在药物治疗的 CTEPH 患者中的预后效用尚未明确,这是一个限制精准管理策略发展的关键知识空白。
为了解决这一未满足的需求,我们进行了一项目标明确的双队列研究,采用两阶段设计:首先,系统筛选一组预先定义的炎症生物标志物(sST2、半乳凝素-3 和一组选定的细胞因子),以评估其与预后的关系;其次,在一个外部独立队列中严格验证最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最终目标是细化风险分层。